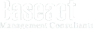2020,是多數組織應對生死存亡的一年。新冠肆虐,給世界經濟按下暫停鍵——隔離、封城、斷航……以防止新冠病毒傳播,這也導致很多企業的市場營銷、生產運營、供應與交付、資金流轉等經營活動幾近停滯。中美貿易戰,進一步加劇了跨國運營企業的供應鏈風險,改變了原有的世界經濟格局和發展趨勢。中觀層面,社會財富分配的馬太效應更為突出,基尼系數攀升,貧富差距持續擴大,社會撕裂,民族民粹抬頭,文明回潮;微觀層面,大企業平臺化整合加劇,資源集中度加大,小企業生存日益艱難。諸多挑戰對企業的經營環境、市場需求、戰略定位、商業模式、供應鏈都造成了巨大壓力。
步入2021,所有人都期待世界能翻開新的一頁,讓生產生活回歸正常。然而,主觀希望是美好的,現實的不確定性卻依然嚴峻。我們認為,2020組織應對的是突發事件的不確定性,如突如其來的新冠,而2021,組織面臨的將是經濟趨勢性、方向性的不確定性,我們總結給出以下三點。
經濟衰退引起的市場不確定性
新冠對社會和經濟造成的創傷,將是長期且目前難以估量的。按照菲利普.科特勒的觀點,此次經濟衰退將至少延續4到7年。所幸多個疫苗研發成功并開始接種,使人們看到工作生活回歸正常的希望。但當英國、美國、上海等地先后出現傳播力更高的變異冠毒時,又讓人們擔憂疫苗對冠毒的免疫效力。不確定導致的社會經濟間歇性、區域性停擺幾率依然較大。
從需求側看,經濟衰退會讓消費者捂住自己的錢袋子,以應對不測之需。這種行為導致:一是原有的市場提前消費驟降;二是非必需品的日常消費量大幅下降;三是在消費過程中,價格敏感度提高,供方只好通過降價確保交易實現。銷售量和銷售價格,是決定企業營收的核心因素,雙雙降低對企業經營活動將造成巨大沖擊。
如果疫情出現反復,除經濟衰退加劇外,會對企業的供應鏈、市場營銷、運營活動造成反復沖擊,直接降低企業供給能力。
高杠桿狀態下市場流動性的不確定
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世界主要經濟體為確保流動性,均進入加杠桿通道,杠桿率持續增高。這次又受到新冠疫情沖擊,各國政府為保障國民基本生活和社會正常運行,確保企業的生產活動,多次發行政府和企業債。根據國際金融協會的數據,截至2020年三季度,全球債務占GDP比率達到創紀錄的365%,發達經濟體債務占比達到432%,較2019年底增長50%。很多大型企業和平臺公司資產負債率已創歷史記錄,“恒大事件”就極具代表性。顯而易見,當利率或匯率稍有抬升,風險會驟增。
2020年12月31日,我國政府為保證流動性,出臺“商業銀行住房貸款集中管理制度”,通過遏制資金流入地產業來確保制造等實體企業的流動性。對企業而言,受市場需求和供應鏈等因素影響,經營性活動產生的現金流與疫情前相比,下降幅度較大。國際金融協會統計數據,截至2020年11月底,G20大企業的營收,較疫情前下降20%,中小企業下滑更達50%。企業營收下滑,疊加巨大的債務壓力,經營難度不言而喻。若債務融資流入的現金流再出現短缺,企業流動性風險必然加劇。我們也就能夠理解政府出臺住房貸款集中管理制度的必要性和及時性了。
另外,隨著疫苗接種普及,疫情逐步得到控制,企業疫情期享受的補貼、貼息貸款、社保和稅收減免等優惠政策會逐步退出,企業經營的流動性可能更加吃緊。因此,2021,企業必須持續加強自身的流動性管理。
疫情等因素對產業鏈沖擊的不確定性
受新冠疫情和國際秩序重構因素影響,大多數產業鏈將面臨重構和遷移。國際關系、供應效率、國家安全是產業鏈重構的主要決定因素。除德國、法國等出口導向型國家外,美國、日本等發達經濟體繼續引導企業回歸本土,或轉移至盟友國家,逆全球化態勢更加顯著。這一趨勢對處于國際產業鏈上的企業而言,供給側和需求側面臨阻斷風險。
為保證國際產業鏈安全平穩運行,推動全球化積極健康向前發展,2020年11月,我國與東盟十國及日韓澳等簽訂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RCEP)協定,12月30日與歐盟簽訂中歐投資協定。在當前復雜的國際經濟形勢下,這兩個協定,對我國的改革開放戰略、國際經濟秩序、國家治理都具有重大的戰略意義,也是實施“雙循環戰略”中“國際循環”的標志性行動。當然,企業在順應國家戰略布局的同時,須明察國際關系變化、文化沖突等對產業鏈帶來的沖擊,做到積極穩妥應對。2020年底的中澳紅酒、煤炭等商品貿易出現摩擦即是典型案例。
2021,作為企業管理者,須審慎洞察組織可能面臨的不確定因素,提前評測和管理這些不確定性,確保組織正常運營。當然,不同組織面臨的不確定性具有一定的差異性,要針對具體企業進行個案分析甄別,但從宏觀和中觀層面看,又都具有一致性,如以上提示的三個不確定性要素。